


生而为人,立于世间,无可奈何。可移动的屏风,给人提供了一种变通手段。毕竟,很多时候你不能砌一堵墙,但你可以有一道屏风。

人通过界定地点,不仅建立了个人的场域,也建立了与他者的关系。



屏风是自身地位的体现,也是对外关系的连接点。在一个由象征意义交织起来的世界里,当屏风与人成为统一体,屏风之上,是这个人最完美的形象。
那么,如果你有一道屏风,你希望在上面如何示人?




到了明代,屏风元素更加流行,戏曲版画、小说刻本插图中常见屏风。
《西厢记》中,“窥视”是一个不断被诠释的主题。比如,屏风的这一边,是崔莺莺正在阅读张生的来信,那一边是正在偷窥的红娘。有的更大胆一些:一边是正在亲热的情人,另一边……还是窥视的红娘。



《韩熙载夜宴图》的创作背景,本就来自多疑的君王对臣子的一次窥探。
韩熙载和他的宾客也明知有人在窥探,却都默许了那一双眼睛,自顾自地进行着表演。
对这一幅图,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关注点。宋徽宗采取的则是对后主李煜全然批判的态度:“……写臣下私亵以观……已自失体,又何必令传于世哉!”
宋徽宗甚至扬言,这样一幅画,丢了也罢!但是他毕竟还是没有把这幅画扔掉。和这次窥探所带来的奇妙互动比起来,窥探本身,似乎就显得没那么不堪了吧。

一轮接一轮的窥探,在历史的情境中,谁又能意识到,自己也已经成为被审视的对象?
宋徽宗那时还没有想到,后主李煜的下场,也将发生在自己身上……
窥探别人不难,难的是在这个无法道破的关系中发现自己。


屏风的幻视力量,激励艺术家去打开玄妙的世界,也令观者心甘情愿沉迷其中。
时空的组合,有无尽的想象。扬·凡艾克的《阿尔诺菲尼的婚礼》远处墙中央的一面镜子,不断吸引人们再凑近一些。委拉斯贵支的《宫娥》中也有一面镜子,让画面里构建的多重空间更富戏剧性。
相比之下,拥有屏风的中国画家,似乎可以走得更远。苏汉臣《靓妆仕女图》里同时出现了镜子和屏风:镜子反射女子的容貌,屏风上的波浪反映的则是她的内心。屏风是另一种“镜子”,它反映的不是客观世界,而是人与世界的隐喻性关联。

中国绘画中“屏中有屏”的设计,还制造了独特的时空交错的效果。
《重屏会棋图》中,现场的人和屏风里的风景互为印证,从男性到女性,从过去到现实,在虚实交替中,彼此观照,不断回旋。既是对时空观的探索,也是对观看心理的挑战。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对世界的感知,有其独到之处。当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用现代性的思辨意识去看,依然新鲜。“重屏”的思维,无论重塑还是解构,仍存在于今天的艺术基因里。传统的经验,也可以成为新创作的资源。
屏风依然有两面,前面是艺术传统,后面是另一种真相。

或许,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真相”,有的只是看事情的方式。
屏风作为一种空间元素,与园林中的山石、照壁、回廊等等,有异曲同工之处。通过阻隔、遮掩,达到隐蔽、变幻、增加深度的效果。
这是一种奇妙的旅程:经由最曲折的路,去最幽僻的地方,那里可能藏纳了人内心里最大的秘密。
事情总是这样。轻而易举、一览无余的,未必能令我们信服;隐藏在深处的,需要不断变通视角的,常常才是奥义所在。


作为一个“外来观光者”,犀利而真诚的毛姆,像个单纯无忌的孩子,常常能够戳中痛点。
他写辛勤的劳动者:
“在中国,驮负重担的不是牲畜,而是活生生的人。”
他写博学而迂腐的大儒:

在这道屏风上,毛姆描绘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中国形象。有眼见为实的真切,又有无法逾越的阻隔。
毛姆写这本书,原本希望它有助于英国读者对中国的想象。时至今日,它又可以帮助中国人去想象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对我们而言,它也成了屏风上的景象。
无论何时,介于真实与想象之间,都有一道屏风横亘在那里。
这个空间,我们从来没有走出去过。屏风,让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不断看见真实,永远心存想象。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誰最中國):相見,如屏。
本文发布者:玩石迷,获取最新内容,请点此关注《顽石有灵》微信公众号。 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anshime.com/32589.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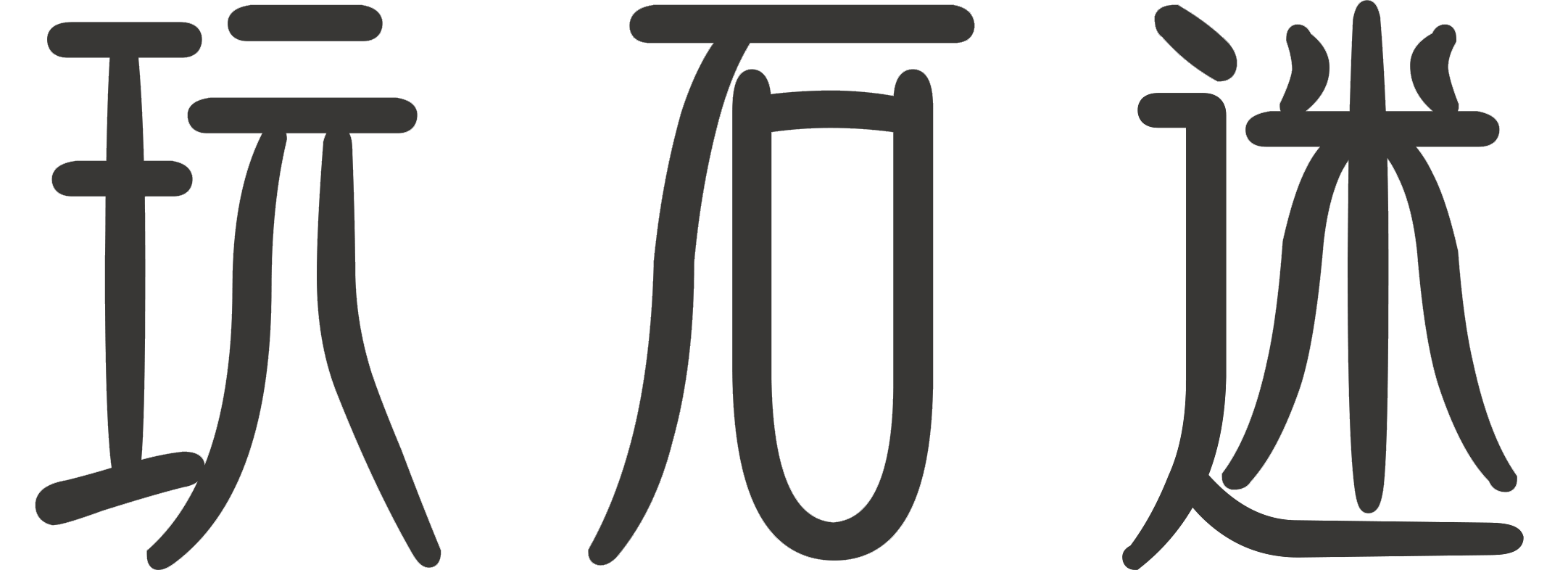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