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可以被确认为唐代的赏石。我们只能通过绘画资料和文献资料对唐代赏石的形象进行推测,而那些图文互见的特质对于揭示唐代赏石形象显然更有可信度和说服力。
在图文互见的特质中,“山形石”是最为常见的,它如此常见,以致于我认为唐代赏石的主要特色就是“山形石”,也正是从稳定的山形结构中我推断出唐代赏石以“端庄”为其美学特征。
一,“石”与“山”的密切联系首先表现在唐代诗词中。唐代诗人往往用形容“山”的语汇形容“石”。例如白居易《双石》:“峭绝高数尺,坳泓容一斗。”《太湖石》:“才高八九尺,势若千万寻。”“远望老嵯峨,近观怪嵚崟。”《奉和思黯相公》:“错落复崔嵬,苍然玉一堆。峰骈仙掌出,罅坼剑门开。峭顶高危矣,盘根下壮哉”。其他如戴叔伦《孤石》:“迥若千仞峰,孤危不盈尺。”王贞白《依韵和干公题庭中太湖石二首》:“山立只盈寻,高奇药圃阴。”姚合《买太湖石》云“我尝游太湖,爱石青嵯峨”。顾非熊《题王使君片石》:“势似孤峰一片成,坐来疑有白云生。”无闷《寒林石屏》:“本向他山求得石,却於石上看他山。”白居易《太湖石》的诗句“三峰具体小,应是华山孙”更为直白,直接把太湖石视为“华山孙”。此外,虽然石的体量远比山小,但唐人所欣赏的“山形石”依然具有“精神欺竹树,气色压亭台”,“岌业形将动,巍峨势欲摧”的气势,因此,这些赏石不仅与山形似而且也达到神似的地步。
“石”与“山”的密切联系还表现在唐诗所用语词上。唐诗描述赏石的语词大都从“山”字,例如“峰”、“峭”、“嵯峨”、“嵚崟”、“崔巍”、“巍峨”等,即都含有“山”的意思。实际上,描述赏石的语词很少以“石”为部首,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语言学现象。换言之,赏石的语汇在很大程度上仍限于“山”的语汇。这更进一步旁证“石”与“山”有紧密的联系。
“石”与“山”的密切联系在现代被证明有着科学上的依据,而并非仅仅是文学上或语言学上的表现手段。分形几何学的研究发现,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着“自相似性”现象。“自相似性”指在不同尺度上物体形态的相似,或者说“部分”的几何形态与它所构成的“整体”的形态相似。用清代沈复的话说就是“大中见小,小中见大”。“石”是“山”的一部分,而二者可以具有“自相似性”,苏轼所谓“五岭莫愁千嶂外,九华今在一壶中”就是这个意思。“石”与“山”在形态上的相似性正是二者密切联系的实质,而这一点似乎很早就被中国人所认识。1996年,美国哈佛大学美术馆为美国雕塑家Richard Rosenblum的中国赏石收藏所出版的专辑,其标题Worlds withinworlds所表达的正是“石”与“山”的这种“自相似性”。
由于这样一种密切的联系,有理由认为,在唐代赏石活动中,赏石者以“石”代“山”,“石”是“山”的缩影,也是“山”的表现。由此可以理解,唐人为什么欣赏“石”,因为“赏石”就是“赏山”(赏均为动词)。
为什么“赏山”?大量唐代诗词表明,唐代以“赏”代“游”,“赏山”实即“游山”。这个“游山”既不是实地涉足也不是远处眺望,而是通过近观“赏石”产生的浮想、联想实现的,中国人称之为“坐游”。“坐游”之所以能实现,就是因为身旁有“赏石”。对此,白居易有一番很好的自问自答。
白居易《太湖石记》有云:“古之达人,皆有所嗜。元晏先生嗜书,嵇中散嗜琴,靖节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无文无声无臭无味,与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众皆怪之,走独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约有云,苟适吾意,其用则多。诚哉是言。适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如果说,“赏石”就是为了满足这种“意”,那么这种“意”又是什么呢?白居易诗《太湖石》也曾问道:“何乃主人意,重之如万金。岂伊造物者,独能知我心。”白居易《太湖石记》进一步答称:“三山五岳,百洞千壑,罗缕蔟缩,尽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为公适意之用也”。对於白居易或牛僧孺来说,“赏石”意在“游山”,山是石的欣赏所在,欣赏是坐游的替代。这就是白居易解读牛僧孺赏石的欣赏取向。
实际上,具有这种欣赏取向而持赏石游山观的人不仅白居易,许多人都是将“赏石”与“游山”相联系的。韩愈《和裴仆射相公假山十一韵》云:“公乎真爱山,看山旦连夕。犹嫌山在眼,不得着脚历。枉语山中人,丐我涧侧石。”姚合《买太湖石》云:“我尝游太湖,爱石青嵯峨。”“置之书房前,晓雾常纷罗。碧光入四邻,墙壁难蔽遮。客来谓我宅,忽若岩之阿。”下面两首诗则写得更为明确。李德裕《题罗浮石》云:“名山何必去,此地有群峰。”齐己《谢主人石笋》云:“从此频吟绕,归山意亦休”。
从这些诗作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诗人在石中所寄托的深厚的山岳情结。这种山岳情结一方面代表着悠久的文化传统。《艺文类聚》引《论语》云:“仁者乐山”,《韩诗外传》云:“仁者何以乐山?山者万物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万物殖焉,飞鸟集焉,走兽休焉,吐生万物而不私焉,出云导风,天地以成,国家以宁,此仁者所以乐山。”另一方面,这种山岳情结也符合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一大批文人“退不入深山”、“不如家池上”的“中隐”生活方式。白居易《中隐》诗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惟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二,既然“赏石=赏山=游山”,“赏石”意在“游山”,为了建立从“石”到“山”、从“赏”到“游”意念上的联系,赏石从形态上就要选择与山岳形似者,“石”因此要具备“山”的基本形态。这就是为什么唐代很多赏石采取了“山形石”的形态。
尽管有那些形容词,因为没有实物证据,我仍不能回答唐代“山形石”的具体形象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这窘困的境地,鲁迅先生也曾提及:“假如有一位精细的读者,请了我去,交给我一枝铅笔和一张纸,说道,‘您老的文章里,说过这山是‘崚嶒’的,那山是‘巉岩’的,那究竟是怎么一副样子呀?您不会画画儿也不要紧,就勾出一点轮廓来给我看看罢。’”“这时我就会腋下出汗,恨无地洞可钻。因为我实在连自己也不知道‘崚嶒’和‘巉岩’究竟是什么样子,这形容词,是从旧书上钞来的,向来就并沒有弄明白,一经切实的考查,就糟了。”所幸古人有画作遗留下来,所以我尚能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之所以称其为“间接”,是因为赏石形象与绘画表现未必等同,但以石入画或按画索石却是合情合理的,因此借助绘画资料了解赏石形象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正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谓“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画。”如果考虑到每一个时代都有特定的审美标准,而这一标准,无论体现在赏石,抑或表现在描述赏石的绘画与诗文中都应该是共通的,特别当画家和诗人同时也是赏石家时更是如此,即如董其昌所云“园可画”、“画可园”,清恽格《南田画跋》亦云“董宗伯云画石之法,曰瘦透漏,看石亦然,即以玩石法画石乃得之。”
首先,我们先看看“山”在唐代前后绘画中的表现及其变化。
山的形象作为背景至少从汉代起就出现于壁画之中,例如山西平陆枣园汉墓壁画。山的形象在传为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辽宁博物馆藏)中继续作为画面背景,或者在《女史箴图》(英国大英博物馆藏,可能为唐代摹本)中作为孤立静物出现。正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说,早期绘画作品中“群峰之势,若钿饰樨栉”,“或人大于山”。在这些早期的绘画作品中有两点与山有关的特点值得注意。第一,所有的山形大体上都呈现为具有稳定感的正三角形。第二,按照传统绘画的象征性原则:物象大小取决于其社会地位或象征意义。由此推知,山在人的心目中尚未占据崇高的地位。
山在人的心目中的地位,至少从绘画角度来看,很可能在隋代发生了变化。在传为隋展子虔《游春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可能为宋代摹本)中,山不再是衬托人物的背景,而是占据画面一个重要的角落,表现得更像崇山峻岭。相应地,山中的人物也变得渺小了。传为初唐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延续了这一表现方式,而在《明皇幸蜀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可能为宋代摹本),山则占据了画面中心位置,成为视觉的主景,渺小的人物穿插其间,呈现出“游山”或“山旅”的情景。至此,山在绘画表现中已经获得一种崇高的地位,并且从正三角形逐渐变为上锐底广的三角形。
然后,我们看看“石”在唐代绘画中的表现及其变化。
日本正仓院藏唐佚名绢画《树下仕女图》,陕西长安初唐韦氏墓出土“六幅屏风壁画”,陕西乾陵博物馆藏初唐《捧盘戏鸟仕女》石刻线画。这三套作品有着相似的画面结构和内容。画面仕女足间的地面上多放置小可手捧的奇石,大体上呈现上小底大的形状,但局部形状变化多端,石表也点缀褶皱和孔洞。由于这些奇石旁大都画有树木,因此可能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云,六朝山水“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也就是说,这些奇石可能直到初唐仍用作仕女、树木和地面的衬托。果如是,这大概是绘画中最早的赏石形象,而且似乎与隋以前绘画中作为人物衬托的“山”,别无二致。

图:陕西长安初唐韦氏墓出土“六幅屏风壁画”
“石”的这种从属的地位似乎延续到盛唐。卢鸿《草堂十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很可能是现存最早的一幅文人画。卢鸿为嵩山的道家隐士。《草堂十志》画面所绘既非六朝“人大于山”的近景,又非后世“人藏于山”的远景,而是中景,即可游、可居之地,是一处人与山石相融合的私家山林。在画面中,人物仍然占据中心的位置,而散布院内的“石”只是体量稍大些,数量更多些而已。有意思的是,草堂环以篱笆,树石散布其间,石与山不分,不知卢鸿是坐石中还是坐山中。由此可见,“石”与“山”有着直观上的紧密联系。

图:卢鸿《草堂十志》
“石”可能从盛唐开始显露出独立的倾向。在传为韩干的《猿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中,树下有一尊山石被刻意描绘。该石块状,石体显得向左倾斜,上部略小,底部略大,左侧下部有向内凹陷形成沟壑,右侧似隆起的脊梁。石体表面点缀细小的涡穴,节理细密,褶皱丰富,表现出遒劲雄浑的质感。由于画面剪裁,因此难以断定这是独立的赏石还是附属于山体的岩石。换言之,“石”与“山”仍有着直观上的紧密联系。

图:韩干《猿马》
到唐代中期,“石”开始有着独立的意境与表现。传为周昉所绘的《簪花仕女图》(辽宁省博物馆藏)很可能是一幅唐代绘画原作。果如是,则卷末的赏石很可能是最早在绘画中表现的独立赏石。从残存画迹看,石与辛夷花相伴,颀然直立如碑,仅在右下部呈现内收外展的曲折变化,表面较平整,略有节理。石与手中的花卉、伺养的小狗、捕获的蝴蝶和宫女都处于“被观赏”的地位,换言之,都属于宫中的玩物。

图:周昉《簪花仕女图》
完整的、独立的赏石形象大概首次出现于1955年河南洛阳出土的唐代“嵌螺钿人物花鸟纹”铜镜(国家博物馆藏)。该铜镜所嵌螺钿湖石呈现山形,人与石同大,石体的褶皱扭曲从阔大的底部盘旋而至顶尖,表现出一种丰满和浑厚的质感。与该铜镜画面相似的是孙位《高逸图》(上海博物馆藏)。孙位,浙江人,生卒年不详,大约活动於晚唐。据考证,这幅《高逸图》应为《竹林七贤图》残卷,绘魏晋“竹林七贤”之山涛、王戎、刘伶、阮籍,缺佚嵇康、向秀、阮咸。通过比较可知“嵌螺钿人物花鸟纹”铜镜所绘应该也属“竹林七贤”的题材。孙位《高逸图》除了以精细严密的笔法描摹竹林贤士的风度神采之外,还以细劲的线条勾勒了两尊赏石。一石位於山涛与王戎之间,上尖下阔,双侧交错内收,不仅使轮廓富於变幻,而且使上部略呈悬垂状;表面具平行倾斜节理,形成直挺的沟壑和褶皱,有少数孔洞穿透其间。另一石立於王戎与刘伶之间,上小下大,左边的凸凹加强了整体造型的变化;石表不仅有或圆或扁的通透孔洞,而且还有因形体的婉转变化巧合而成的各种半洞,石洞内可见罗纹和凸隆。两尊赏石都经过墨色渲染,但就质地而言,前者显得坚脆,後者则显得柔韧。前者与芭蕉相伴,後者为竹林掩盖,象贤士一样席地而坐。

图:唐代“嵌螺钿人物花鸟纹”铜镜

图:孙位《高逸图》
上述“竹林七贤”图中的赏石值得深入的研究。首先,无论是铜镜还是图卷,都有比例较小的侍女或侍童出现,说明其画面仍然遵循传统绘画的象征性原则。由于赏石的体量似乎与人物同大或略大,因此推知,山石在人物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变得重要起来。其次,这些赏石都呈现为上小下大的山形。石的轮廓变化和孔洞布局服从於“山”的稳定性要求,例如孙位《高逸图》中第一座赏石,上部的悬垂与左下部外展的小石峰相平衡;第二座赏石,虽然左部大於右部,但左部的孔洞与右部的重实相平衡。按照前述“赏石=赏山”的理论,这些“石”应该暗指“山”。显然,这种暗指可以被“竹林七贤”的主题所印证。尽管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只是在竹林中喝酒、弹琴、纵歌,并未逃逸“山”中,但后世通常认为“竹林七贤”代表的是一种隐逸文化,因此,选择“山”表示隐逸是合乎情理的。最后,“游山”是“坐游”,并非真正地逃遁山林。画面中赏石略微谦卑的体量以及与人物的穿插旁列,暗示着这些高逸的贤士也只是“坐游”而已。这与唐代诗词所揭示的“赏山=游山”是完全一致的。根据上述分析,有比较充分的理由将孙位《高逸图》中的两尊赏石视为唐代赏石形象的典型代表。
一九五九年,陕西西安出土了一件唐代“三彩陶山池”。这件“三彩陶山池”立於墓葬中一个摹拟的庭院里,虽然可能是庭院中叠石或堆土而成的假山,但仍不妨将它看作“山形石”。此石高十八厘米,宽十六厘米,呈现出唐诗或唐画中所见的上小下大的山形,山势陡峭险峻、层峦叠嶂,脉络婉转流畅、起伏回环。这与六朝以来包括壁画在内的绘画中所见的紧劲联绵、圆浑婉转的山石形象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可以作为上述唐代赏石形象的有效参照。
对于佐证我的“赏石=赏山=游山”理论来说,没有什么绘画证据比卫贤的《高士图》更可靠。南唐卫贤《高士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是为数不多的公认为晚唐五代的作品之一。卫贤,生卒年不详,陕西人,以界画著称。该图绘汉代隐士梁鸿与妻孟光“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故事。图中以细线勾勒一巨大赏石立於庭园之中:石体直立如碑、节理整饬,显得挺拔端庄;大片留白表现出石表的平滑,乾笔皴染起伏曲折之处,则显得苍劲嶙峋、雄厚壮观。

图:卫贤的《高士图》
现在我们仔细研究《高士图》画面中的赏石。第一,在崇山峻岭的屋舍旁竖立一尊赏石是超乎常理的,因此合理的推测是,屋舍旁的赏石是真实的,而屋舍后的高山则是假想的。第二,赏石与高山的形状、气势、节理具有很强的相似性。高山仿佛是赏石放大的“镜像”。这个相似性一方面为“石”与“山”的对应或者“赏石=赏山”的理论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则旁证上述第一条的推测是正确的。第三,按照前述“赏石=赏山”的理论,这尊赏石应该暗指“山”。显然,卫贤并未像孙位《高逸图》那样采用暗指的手法,而是直接在屋舍背后画出高山。对于宣扬纲常伦理的说教画来说,采用这种使隐喻对象一目了然的表现手法是不难理解的。这就反过来印证了“赏石=赏山”的理论。显然,中国古人不仅发现了“石”与“山”之间的相似性,而且还利用这种相似性。第四,理查•施特劳斯在《查拉图斯特如是说》中通过音高级进上行的方式描述太阳升起的景象。类似地,卫贤《高士图》则采用赏石—人物/屋舍—树木—山峰逐级升高的手法,通过“坐游”即“赏山=游山”的方式,表现纲常伦理不可撼动、不可逾越的至高地位。将石置于屋舍旁就意味这个隐喻过程正是通过“赏石=赏山=游山”实现的。这就印证了我的“赏石=赏山=游山”理论。第五,在这样一个隐喻的过程中,“石”承担着媒介、联想、象征的功能。由于重要性增大了,所以与卢鸿《草堂十志》相比,“石”开始侵入画面中心的位置,而与孙位《高逸图》相比,“石”已经显著地大于人。这使得我的“赏石=赏山=游山”理论在这幅画作中表现地更明确,更直接。
三,除“山形石”以外,唐代诗词还记述了赏石的许多其他特质,这些特质在唐代已经成为赏石重要的欣赏要素。例如,许多赏石的表面多凸凹、曲折,呈现出沟壑、淙注、鳞皴、浪纹、缕络、虫篆、抓痕等多种形态,唐诗称为“背面淙注痕,孔隙若琢磨”、“霹雳划深龙旧攫,屈槃痕浅虎新抓”、“云根劈裂雷斧痕,龙泉切璞青皮皴”。还有许多赏石具有嵌空、宏大的孔洞,唐诗称为“嵌空华阳洞”、“坳泓容一斗”、“风气通岩穴”、“透穴洞天明”。吴融的《太湖石歌》描述得更为生动:“雨过上停泓,风来中有隙。”“所奇者嵌空”,追逐“嵌空”的时尚在唐代如此泛滥似乎影响到绘画的表现,以致晚唐张彦远评绘画之石,认为嵌空有余,“务於雕透,如冰澌斧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代诗词中不仅出现“通透”,而且也出现“皴皱”、“形瘦”甚至“厥状怪且丑”等语汇,说明在后世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些赏石欣赏观念早在唐代就产生了。
尽管有这些文字上的描述,由于既没有实物也没有绘画资料,我们对于“山形石”以外的赏石具体形象仍然不得而知。这类赏石直到五代时期才第一次出现在绘画作品之中。後蜀滕昌祐的《蝶戏长春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为我们了解这类赏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图:滕昌祐的《蝶戏长春图》
滕昌祐,生卒年不详,江苏人,擅长花鸟草虫。《蝶戏长春图》对角线下的部分由湖石组成,其中位于左角最大的一尊湖石,体态圆浑丰满,虽右侧内收,大体上呈现对称的五角星状而不是山字形。石体表面窍孔盘踞,辗转钩连。孔洞变化多端,而洞道内外涟漪的水纹和波浪的轮廓,更使此石显得婀娜多姿,美轮美奂。赏石表面曲折婉转的线条变化所展现的玲珑剔透的视觉效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於绘画的没骨技法,但它与张彦远对绘石“务於雕透,如冰澌斧刃”的批评颇为吻合,因此很可能是晚唐以来在“山形石”以外的那类赏石形象的具体写照。《蝶戏长春图》所绘赏石并非孤例。五代王处直墓後室北壁中央有一幅壁画《牡丹图》,所绘奇石双侧轮廓相向收展而成品字形,孔洞和褶皱更为夸张、怪异。

图:王处直墓《牡丹图》
将上述两图中的赏石形象与孙位《高逸图》所绘赏石相比,可以明显地发现,赏石的装饰性和奇异化在五代时期显著地增强了。在宋代赏石形象的研究中,我们将进一步说明,这种装饰性和奇异化成为中国赏石在唐代以后发展的主要动力。
上述论述试图说明的是,首先,与自然的“平衡”与“和谐”从远古以来似乎都被认为可以导致情感的愉悦,因此是美的;古希腊直到文艺复兴,则将任何“对称”与“和谐”都视为美的。唐代以“山形石”为代表的赏石,从形象和文献资料来看,的确有着一种和谐、端庄的美感。其次,从初唐昭陵六骏所见的为大唐帝国立下汗马功劳威武雄健的战马形象,到一个世纪后韩干所绘唐玄宗马厩里膘肥体胖的西域骏马良驹,其中的差别正是初唐到盛唐的转变。唐代赏石似乎至迟到晚唐五代也向着这种装饰性和奇异化的方向变化,大概一如张彦远对晚唐绘画的责难:“无生动之可拟,无气韵之可侔。”最后,唐石将跻身于唐诗、唐画、唐音、唐构之列,成为中国艺术鼎峰的重要组成部分。唐石是中国赏石之正宗,是东亚各国赏石文化之源,因此搜集唐石实物、研究唐石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祈盼后学努力!
本人偏安小岛,拙著《中国古代赏石》出版二十年来的新资料难以遍览,致使拙文不免舛误,敬请有心读者斧正。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丁文父):唐诗、唐画与唐石
本文发布者:玩石迷,获取最新内容,请点此关注《顽石有灵》微信公众号。 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anshime.com/21147.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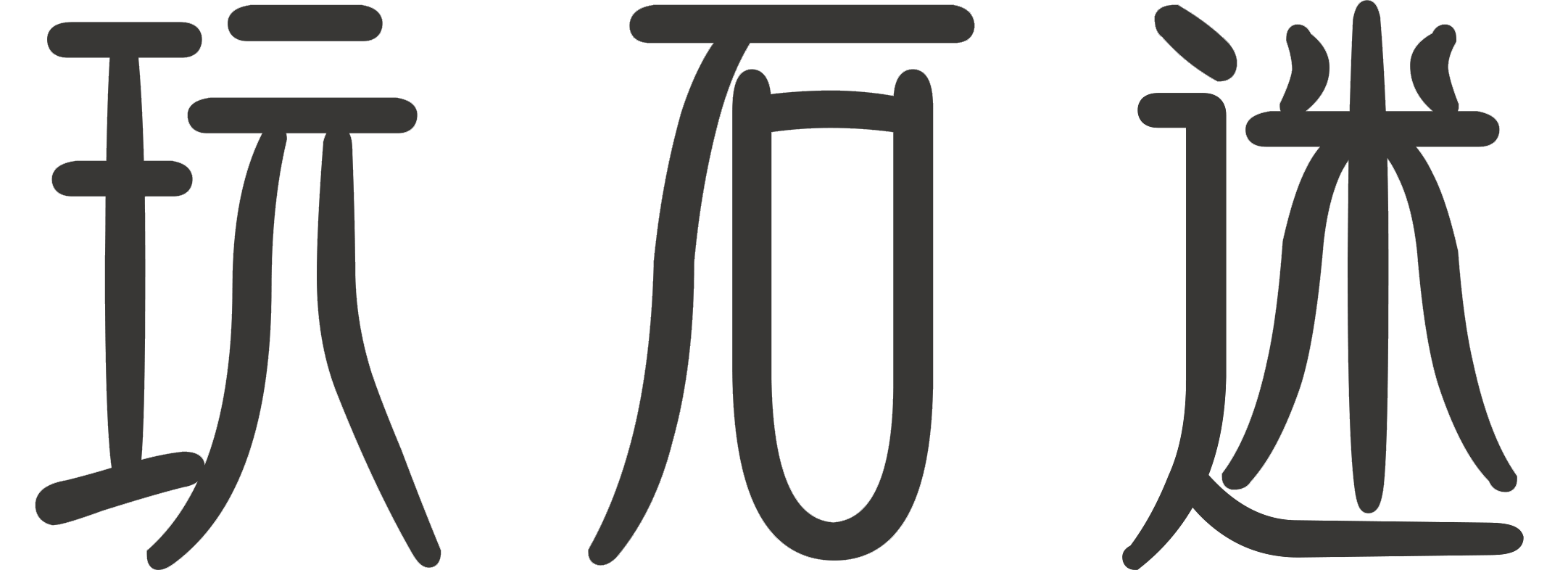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