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明确记载赏石的文献资料以诗文为主。这些诗文大都属於盛唐到晚唐这大约两百年间,兴诗作文者也大都是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因此有关唐代早期以及文人士大夫以外的奇石欣赏便不得而知。有意思的是,唐代著名诗人杜甫是禅宗的信徒、李白是道教的方士,此二人似无赏石之乐。《素园石谱》称“小祝融”为杜甫所藏,不知何据;李白一生漫游隐居,咏山林景致、人物交往,“一身自潇洒,万物何嚣喧”,似乎没有留下任何咏石的作品。
从唐代诗文来看,当时赏石的体量小型、中型、大型俱备。小型者,如戴叔伦《孤石》:“迥若千仞峰,孤危不盈尺”;中型者,如白居易《磐石铭》:“客从山来,遗我磐石。圆平腻滑,广袤六尺”,王贞白《依韵和干公题庭中太湖石二首》:“山立只盈寻,高奇药圃阴”;大型者,如白居易《太湖石记》:“高者仅数仞,重者殆千钧”。在这三种体量中,虽然大型可能不在少数,例如後人记李德裕平泉庄“怪石名品甚众”,“有礼星石”,注云“礼星石,纵广一丈,厚尺余”,但似乎仍以中型为普遍,如白居易《双石》:“峭绝高数尺,坳泓容一斗”、《太湖石》:“才高八九尺,势若千万寻”。案唐尺略短於今尺:一尺约合二百八十至三百一十三毫米,仞高八尺,八尺曰寻。尽管仞的尺度较随意,但唐诗中有关赏石体量的尺度仍然是较为真实的,特别是在诸如“迥若千仞峰”“势若千万寻”这样的夸张衬托下就更显得可信。
根据唐代诗文的记载,赏石的形状可以大体上分为三种:一为山峰形,二为动物或人物形,三为规整体。唐代赏石许多被描述为山峰的形象。唐汧国公李勉之子李约曾於润州海门山得石如两座山峰故名“双峰石”。白居易诗《太湖石》云:“远望老嵯峨,近观怪嵌崟”,另《太湖石》云:“三峰具体小,应是华山孙”、《奉和思黯相公》:“错落复崔嵬,苍然玉一堆。峰骈仙掌出,罅坼剑门开。峭顶高危矣,盘根下壮哉”。虽然石的体量远比山小,但唐人所欣赏的山形石仍然很讲究山的精神气势,所谓“精神欺竹树,气色压亭台”“岌业形将动,巍峨势欲摧”。唐代还有很多赏石貌似动物或人物,欣赏者也每每以动物或人物相类比。吴融《太湖石歌》自问自答,费尽千辛万苦从太湖中捞取幽石,其奇形怪状谁能识别呢:“初疑朝家正人立,又如战士方狙击。又如防风死後骨,又如於菟活时额”。白居易看过丞相牛僧孺的赏石收藏,作《太湖石记》云:“有端严挺立,如真官神人者”,“又有如虬如凤,若跧若动,将翔将踊;如鬼如兽,若行若骤,将攫将鬥”。宋人记李德裕平泉庄,有“狮子石,高三四尺,孔窍千万,递相通贯,如狮子,首尾眼鼻皆全”。皮日休从鼋头山得太湖石而作《太湖石》云:“或拳若虺蜴,或蹲如虎貙。联络若钩锁,重叠如萼跗。或若巨人骼,或如太帝符”。尽管这些描述多采用比拟或夸张的手法,而不尽然类物象形,但表达的却是赏石形象有如动物或人物的那种生龙活虎的生气:“掀蹲龙虎鬥,挟怪鬼神惊”、“突险呀空龙虎蹲,由来英气蓄寒根”。这种描述与其说是借动物之形,毋宁说是扬动物之势,其实质就是利用动物的形象表达赏石所具有的生动气势。最後一类赏石为柱状、板状、块状,造型较为规整。柱状者多为石笋,其观念大概起源於擎天柱石。崔全素《石笋高》云:“石笋生孤标,屹立青冥直”,刘昭禹《石笋》:“千古海门石,移归吟叟居。窍腥蛟出後,形瘦浪冲余”。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後世欣赏标志的“形瘦”在这里偶被提及。板状者又称石板。李咸用《石版歌》:“直方挺质贞且真,当庭卓立凝顽神”。块状者常为磐石。太和九年夏,有山客赠白居易磐石:“圆平腻滑”,另有“弘农杨贞一与青石三,方长平滑”。
赏石表面作为美感要素的孔洞、窝陷、沟迴、纹理以及一些次生现象等在唐代已经受到关注,对此,唐代诗文中有大量的描述。首先,赏石表面的洞穴多嵌空、宏大,描述者如“嵌空华阳洞”、“坳泓容一斗”、“风气通岩穴”、“透穴洞天明”。吴融和王贞白的描述更为形象,吴融《太湖石歌》云:“雨过上停泓,风来中有隙”;王贞白《依韵和干公题庭中太湖石二首》云:“风涛打欲碎,岩穴蜇方深”。嵌空宏大的孔穴更容易容纳万千气象,以故白居易《太湖石记》写道:“风烈雨晦之夕,洞穴开皑,若合云歕雷,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其次,赏石表面的纹沟多凸凹、曲折,并呈现出淙注、鳞次、浪纹、缕络、虫篆、抓痕等多种形态,例如姚合《买太湖石》:“背面淙注痕,孔隙若琢磨”、李德裕《叠石》:“鳞次冠烟霞,蝉联叠波浪”、姚合《天竺寺殿前立石》:“霹雳划深龙旧攫,屈槃痕浅虎新抓”、李咸用《石版歌》:“云根劈裂雷斧痕,龙泉切璞青皮皴”。牛僧孺记友赠奇状绝伦之太湖石:“缕络钓丝萦”“通身鳞甲隐”,白居易和刘禹锡奉和之作,也采用几乎同样的描述:“隐起磷磷状,凝成瑟瑟胚”、“拂拭鱼鳞见”“纤鋩虫篆铭”。值得注意的是,李咸用的《石版歌》明确提到了赏石表面的“青皮皴”,这个“皴”字被後世用於概括赏石表面如上所述的种种形态。当然,并非所有的赏石都具有这种“皴”的特征,形状规整的赏石表面往往比较平滑,例如白居易的藏石:“圆平腻滑”、“方长平滑,可以坐卧”。最後,赏石表面的次生现象例如苔藓、痕渍在唐代有着格外的观赏意义,有关的描述不绝於耳,例如,杨巨源《秋日韦少府厅池上咏石》:“旧溪红藓在,秋水绿痕生”、李咸用《石版》:“古藓小青钱,尘中看野色”、白居易《双石》:“孔黑烟痕深,罅青苔色厚”、刘禹锡《和牛相公》:“烟波含宿润,苔藓助新青”、郑损《星精石》:“苍苔点染云生靥,老雨淋漓铁渍痕”、褚载《移石》:“浪浸多年苔色在,洗来今日碏痕深”。
唐代文献中有关赏石颜色的记载极为少见,而有关赏石质地的记述也寥寥无几,并且通常都是以“玉”比照、以“音”衡量的。例如,李德裕《题奇石》:“蕴玉抱清辉,闲庭日潇洒”、李勋《泗滨得石磬》:“出水见贞质,在悬含玉音”、褚载《移石》:“磨看粹色何殊玉,敲有奇声直异金”,牛僧孺、白居易、刘禹锡三人共咏的太湖石也若“苍然玉一堆”,轻敲而声音“清越扣琼瑰”“铿锵玉韵聆”(原载拙著《中国古代赏石》,转载于此略有修改)。
批判:
第一,拙著收集文献资料不够充分,过于依赖文学资料,实际上唐代文献遗存中文学只占很小的部分,地方史志、出土文献、宗教文献、域外汉籍,特别是敦煌资料未曾顾及,这是一大缺憾。
第二,唐代诗文年代可靠性未曾详考,这是研究“程序”上的重要瑕疵。
第三,诗文等文献资料的解读不够深入。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丁文父):文献资料所见的唐代赏石
本文发布者:玩石迷,获取最新内容,请点此关注《顽石有灵》微信公众号。 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anshime.com/20094.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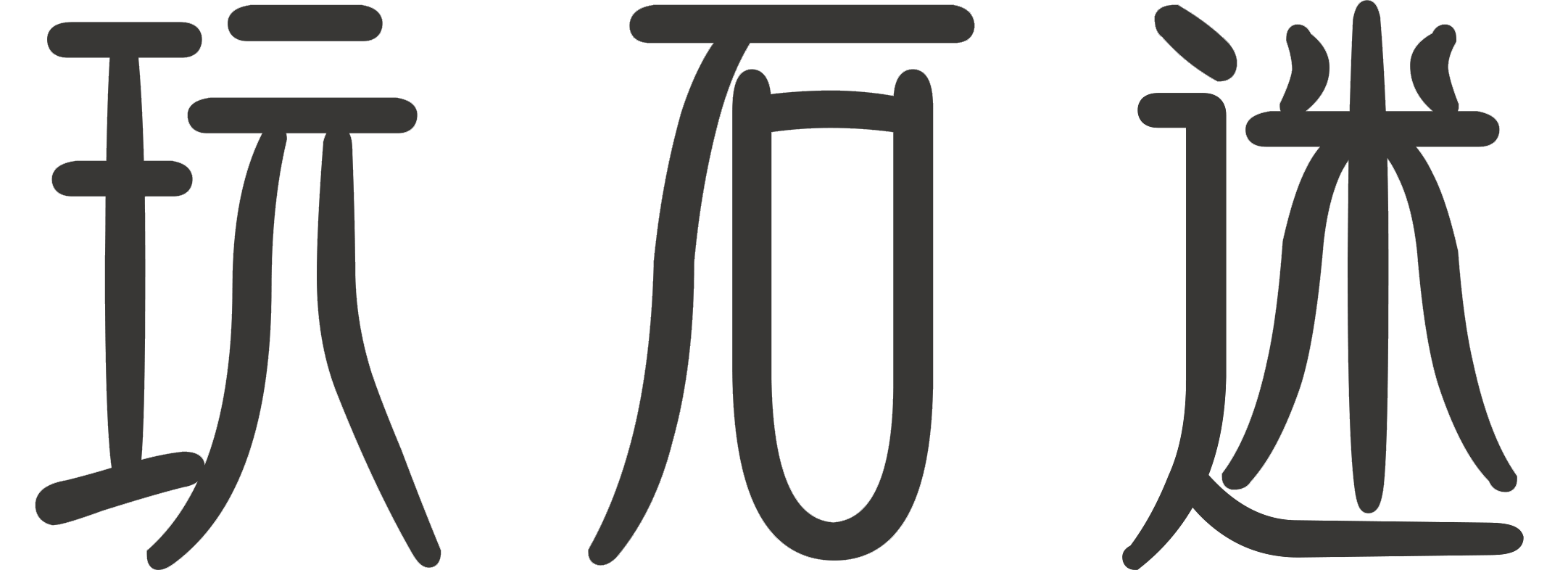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