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先生抽完一支烟,带着遗书,跳入了颐和园昆明湖。打捞上来的遗书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陈寅恪先生所撰挽词则解释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由此算是对王国维先生的死因给出一个合理的交代。这也使得年轻的我从此明悟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的人文学者大抵分为“欠死的”与“不欠死的”。所谓“不欠死的”,据陈寅恪先生所称推理,就是对文化衰落不“感苦痛”之人,“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微,因此方能苟且偷生仍可“求一己之心安”,更无惮于是否“义尽”。因此,我对王国维先生的敬重也就转变为对那些活着仍自称“国学者”的轻鄙,仿佛“先生”、“教授”都是一种谥名,若是不跳湖都名不符实。也因此至今都害怕被人称为“先生”或“丁老”,仿佛要逼我也去寻湖。

及至年长方渐渐懂得这样的分类也断无道理。人之生权乃上帝所予,而在万难的境遇中小心翼翼地保全人格倒也颇需一番勇气与坚持。例如陈寅恪先生,他当然也属“欠死之人”,故有“只余未死一悲歌”之咏,但“欠死”而“未死”,在那样的困顿中一边喘息,一边书写着“柳如是”,倒真是暗泣鬼神的勇士。这使得我慢慢地恢复了对这些人文学者的敬重,而且这种敬重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渐渐浓厚起来,使得我现在回想起上个世纪80和90年代,虽然巨星大都陨落,但天空星星点点,依然璀璨,仍有许多值得怀念的人文学者。
哲学家里最值得怀念的是梁漱溟(1893—1988)先生。梁先生早年住辟才胡同,晚年被安排住到北京复兴门外大街那座著名的22号楼里。北平“解放”不久,他去探望我的老师,未果,留下著作和信签一封,上有辟才胡同的地址和电话。这本书后来由我的老师转赠给我,成为我“辍读”之后保留的极少数图书之一。梁先生为人极为平和,但讲起过去在政协会上的仗义执言仍然慷慨激昂。后来,我自恃初生牛犊,用从梁先生处学到的“雅量”一词揶揄我的系主任,遂招致“退学”之祸。但我每每想起梁先生的谈吐依然充满着无尽的享受。

那时候在北大校园里偶尔能见到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但我去燕南园“三松堂”与其说是见冯友兰先生,不如说是想一睹冯先生女儿宗璞的芳容。宗璞的《红豆》给我留下的印象远比冯先生的音容笑貌深刻。对于冯先生,我只记住了他蓝衣大褂上常常粘着饭粒。
李泽厚算是后学了。我忘记为什么去过他在北京和平里九区的煤矿文工团宿舍。对于他的书,读过了也忘记了。
文学家里最值得怀念的是沈从文(1902—1988)先生。我那个年代不时兴追星,因此与大文人们交往从来也不会想到合影留念。不过,不知是谁拍摄的,我居然保留着一张与沈从文先生的合影。沈先生言谈举止极为柔和,颇有“大家闺秀”的气度,不知道是不是受夫人张兆和先生的影响。沈从文先生教书时爱上了女学生张兆和,写过不少情书,令张允和不胜其烦,遂状告校长胡适。尽管如此,张兆和最终抵挡不住那些情书,还是嫁给了沈先生。据说,那些情书实在是“写得太好了”!沈先生也住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2号楼,家徒四壁,只有一具小木柜像是沈先生同龄之物。近年有内幕消息传出来,中国文学家中最早接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不是那个老舍,而是沈从文先生,因为早在1949年以前,沈先生的小说就已经被瑞典方面关注了。

梁漱溟和沈从文二位先生都是在“那一年”之前离世的,这多少让他们免除了更多的忧伤与苦恼,是为庆幸。
我接触的文学界其他老人有家住北京东罗圈胡同、翻译普希金的戈宝权(1913—2000)和家住北京虎坊路、翻译列宁传的毕朔望(1918—1999),但对他们我已经没有任何印象。听说戈宝权先生1979年写下轰动京城的《只因……》。
因为学业的关系,我接触最多的是人类学和社会学家,其中让我永生不忘的是李景汉(1895—1986)先生。李先生1917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修社会学,回国后成为清华大学教授。上个世纪80年代,我许多周末都是在李先生位于北京团结湖北三条的家中度过的,一是帮助他整理旧著,二是为了蹭饭,因为他后来的妻子做饭实在是太好吃了。在李先生去世前两年,李先生不仅“资助”我的学业,而且还经常送书给我,让我对欧美的社会学研究有了不少的了解,例如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甘博等人的研究。

在学术方法上与李景汉先生极为不同的是人类学家费孝通(1910—2005)。费孝通1936年赴英,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人类学,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教授。费先生秉持的是人类学部落研究的方法,往往依靠“讲述”而不是李景汉先生所用的数字来解释社会现象。费先生的课听起来是轻松的,但真正理解却是费力的,因此他的作业我很难完成。有一次,他要求我们写不少于30页的论文。我苦思苦想难凑其数,只好每页写8个字交上去。课堂讨论的时候,费先生看着我写的论文,捏着他嘴边的一撮毛迟迟不语,而我则忐忑不安生怕他一怒之下扭断那撮毛。最后,他只淡淡地说:“你是担心我眼花吧!”我后来想,那个时候他一定下决心不要我这个学生了!实际上,我对费先生的热衷朝政非常反感,但我也不得不常去他在民族学院和平楼的家中——除了因为上课,女生若有问题,不敢独自前往,因为费师母会令人非常尴尬地坐在女学生与费先生之间。据说女生离开后,费先生的日子也就不平静了。因此,她们总是知趣地叫上男生一同前往费宅。
北京的民族学院在院校调整后聚集了一大批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那些教育官员们也搞不懂这些人是研究什么的,大概只因为他们是“少数”的,所以就把他们打发到专门研究“少数”的民族学院了。这些老教授里最年长的是吴泽霖(1898—1990)先生。吴泽霖先生1922年赴美,入威斯康辛大学修人类学,回国后成为清华大学教授。另一位是吴文藻(1901—1985)先生。吴文藻先生1923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学社会学,回国后成为清华大学教授。吴文藻先生是费孝通先生的老师,他的夫人则是著名的作家谢冰心。吴先生与费先生是邻居,我去吴先生家从来没有面见谢冰心先生。说实话,我也不太喜欢谢冰心的作品。
民族学院的老教授中,我比较喜欢杨堃(1901—1998)先生。杨先生1921年赴法,入里昂中法大学修人类学,回国后成为清华大学教授。杨先生为人非常朴实。另一位我比较喜欢的教授是林耀华(1910—2000)先生。林先生1940年获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回国后成为燕京大学教授。林先生的学问非常好,我申请美国大学研究生的多封推荐信就是林先生写的。
与上述所有这些老教授们不同的是雷洁琼(1905—2011)先生。雷先生既不住在人民大学,也不住在民族学院。大概作为少有的女性社会活动家,雷先生享受本朝的优待,一直住在红墙外的红霞公寓。雷先生1931年赴美,入南加州大学修社会学,回国后成为燕京大学教授。我不记得她给我们上过课,我甚至不知道她写过什么著作,除了那些奉和之作以外。
著名经济学家中有过一些交往的有如下几位教授。陈翰笙(1897—2004)先生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1921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1924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回国后成为北京大学教授。陈先生是1925年的中共党员,堪称中国左派经济学家以及计划经济学理论的鼻祖。陈先生家住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4号楼,似乎陈永贵也住在这里。电梯里偶遇“陈副总理”,有时尴尬地不知如何称呼。南开大学教授傅筑夫(1902—1985)先生1936年赴英,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史和经济学。傅先生气宇轩昂,学成归国后似乎一直都在收集整理经济史资料,很少著文撰说,积几十年之功,只为写作《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遗憾的是终未完成。傅筑夫先生“孤注”竟有“一掷”,而北京大学的陈岱孙(1900—1997)教授就鲜有著述。陈先生1920年赴美,入威斯康辛大学学经济学,后入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我不记得是否去过陈先生的家中,但我至今保留着他在北大镜春园79号的地址。陈先生为人处事极为清静。我的同学后来成为他的研究生。她告诉我当年陈先生着白色西服,骑白色骏马,着实是绅士做派。陈先生是末代皇帝溥仪帝师陈宝琛的族人,而我也与陈先生亲属相熟,因此知她所言不妄。
我很难想象像傅先生与陈先生这样述而寡作的教授在今日的大学里可以生存下去。
北京大学还有一些老教授曾经在学业上给予我很大帮助。例如,我去甘肃敦煌沙漠进行古人类生态考察就得到侯仁之(1911—2013)教授的支持。侯先生1946年赴英,入利物浦大学学习地理学,成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地理学派的开创者,与在复旦大学的历史地理研究之文献学派的导师谭其骧南北相对。侯仁之先生住北大燕南园61号,我隐约记得61号有一部分自文革被占据后一直没有归还给侯先生。我的考古学知识中汉唐部分来自于俞伟超(1933—2003)先生。俞先生上课时总要让我们画各种坛坛罐罐,名之为类型学。这是艺术史研究中最为基础的课程,也是风格研究的基础,可惜我一直没有学好。隋唐部分来自于宿白(1922—2018)先生。宿先生上课时基本上就是念讲义,我们也只能低头速记。如果这门课是上午,还比较好;如果是下午,那基本上就是昏昏欲睡。我那个时候就在想:与其钞稿,不如回宿舍看书。宿先生既重实物又重文献,是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的忠实执行者。他的初版《白沙宋墓》我保留至今。我的古生物学知识则来源于杨式溥(1925—2002)教授。杨先生为人和蔼,知识渊博,他使得我后来非常喜欢古动物和植物化石,我甚至还把这个兴趣传给了儿子。杨先生当时属于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的教授,只是在北大代课。我被“退学”之后,杨先生也曾极力帮我周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王永兴(1914—2008)先生。王先生受教于陈寅恪先生,曾担任陈寅恪先生助手多年,也曾经受多年的迫害。虽然他1978年调入北大,但一直蜗居于未名湖北畔的健斋,似乎多年也没有教授的职称。我为了敦煌文书的事情常去他逼仄的小屋拜访,他对我这个难称学生的后学依然耐心指教,使我受益匪浅。后来,听说他以70多岁的高龄娶入年轻的女学生,在流离颠沛的生活中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家。
其实,我求学期间最为崇拜的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杨锺健(1897—1979)、裴文中(1904—1982)、吴汝康(1916—2006)三位人类学家。杨先生1923年赴德国学习古脊椎动物学,1927年获得慕尼黑大学博士,回国后指导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发掘工作。裴先生1937年获法国巴黎大学博士,他1929年主持周口店的发掘,是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者。吴先生1949年获得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博士。吴先生是解剖学出身,所以他写的论文非常严谨。我曾经想改学古人类学,以实现我多年“古多尔”式的梦想,但生不逢时。后来在中科院古人类所比较年轻的老师袁振新、许香亭、尤玉柱、侯连海等人的帮助下,我还是开始了自学,因此读过上述三位老教授的许多论文。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尚未封闭时,我时常一个人钻到山顶洞人的山洞里,希望也发现人骨化石。
还有一些亦师亦友的老先生是我一直难忘的。首先是王予予(“予予”为单字,读xu,电脑及普通词典都未收此字)先生。我很早就认识王先生了。王先生是沈从文先生的助手,也是社科院考古所里极富献身精神的专家。我对于考古学的兴趣大概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启蒙的。他费时多年利用业余时间为我修复的“明万历帝御赐布达拉宫幡头”(据称是存世最大最老的幡头)至今留在我的居室之中。其次是著名的大右派葛佩琦(1911—1993)教授。我与葛先生结识于医院,他以亲身经历给我的肺腑之言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而这个肺腑之言是难以外传的。最后是王世襄(1914—2009)先生与朱家溍(1914—2003)先生。他们是我以“玩”为业的老师与朋友。朱先生讥我“非读书,用书而已”,王先生更直言“你玩都不会,还能会什么”。这些话至今仍回荡耳际。近年常有人对我说:你与二位先生很熟识,为何不也写一些纪念文章?我对于利用名人“弘扬”自己毫无兴致。我甚至把王世襄先生和朱家溍先生给我写的题签都送给年轻的朋友了。我在玩的过程中得到两位先生的帮助已经让我受益匪浅,为什么我还要打扰他们的在天之灵呢?!前些日子整理书库,又翻检出王世襄先生信函一封。若有索要者,告知,赠送之。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凌子风(1917—1999)先生拍完《骆驼祥子》后意犹未尽,一直寻找机会实现他多年来给北京“天桥”拍一部影片的愿望。我给他看了我老师保存的一套天桥老照片,他特别兴奋,希望我帮他实现他多年的愿望。1984年他妻子石联星去世,我因为常去凌先生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家中,与石伯母也熟悉,因此打电话问候凌先生。电话中,凌先生却告诉我他又结婚了,让我一时语塞,不知是否应该说“祝贺”之类的话。
后来吴祖光(1917—2003)先生闻知后也对“天桥”的事情颇感兴趣。吴先生的妻子新凤霞是从天桥出来的艺人,吴先生那时正在帮助新凤霞写回忆录,夫妇二人都对“天桥”留有格外的情感。吴先生家住北京工体东路,在当时也算是僻静之处——这对于身体不好的新凤霞来说非常重要,现在则是闹市中的喧嚣之地。
再后来三联书店的“三多”(书多,酒多,朋友多)老板范用先生也参与到“天桥”的谋划之中。范先生非常和蔼可亲,他的办公室里除了书就是书,没有酒瓶。后来我听王世襄先生讲起范用先生来家中比试做菜的手艺。菜一端上来,范先生必先大快朵颐,害得王先生撂下锅,忙不迭地奔回桌旁。王先生说,转身的功夫,盘子已经一扫而光。范用先生去世之后,“出版家”这个名词也就可以从字典里摘除了。
戏剧家乔羽先生是个非常风趣的人物。30多年前我与他一起吃过一次涮羊肉。他在桌旁说的一句话让我清晰地记到现在:“人生之悲剧莫过于把妻子变成朋友,或者把朋友变成妻子。”大家自己去体会吧。乔先生今年已经92岁高龄,几乎是我交往过的老先生中唯一的幸存者。我在遥远的孤岛上祝他健康、幸福、更加长寿。
……
中国文化学术之研究,根植于宋代,枯竭与元明,强固于清朝,海纳于民国。己丑之后,学术者尽享前朝之荫庇,而我们那一代的学生,正如我的舍友葛兆光所言:尚能享受这些老师的余泽。尽管这些老师未必能与王国维先生相提并论,但今日回望,倒也是蔚然大树,而且似乎这些大树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高大起来,因为俯视当下,没有了“独立之精神”的天空,没有了“自由之思想”的地壤,我们再也看不到小树的萌发和成长。一眼望去,荒原茫茫……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丁文父):王国维投湖之后
本文发布者:玩石迷,获取最新内容,请点此关注《顽石有灵》微信公众号。 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anshime.com/21944.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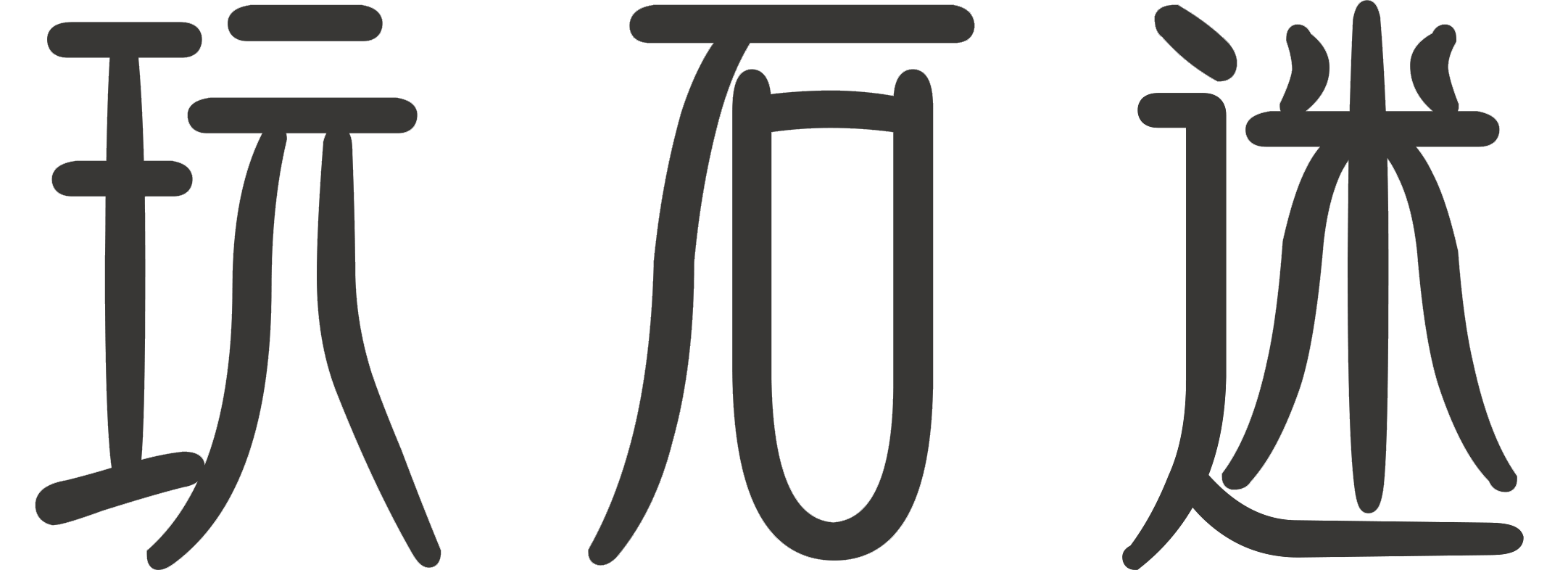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