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赏石艺术源远流长,但流传至今形成审美疲劳恐怕是不争的事实。造成这种审美疲劳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不想从“美”的角度进行回答。钱钟书曾引用伏尔泰何谓美之问:“询之雄蛤蟆,必答曰‘雌蛤蟆是也’”。毛嫱丽姬之美,乃沉鱼落雁之丑,难有一定之规。因此,我倒愿意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反思有关赏石艺术的两个基本问题:赏石是不是艺术?赏石是什么样的艺术?本文分为多篇连续发表,各篇独立成章,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更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第一个问题:赏石是不是艺术?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先明确什么是艺术。如何定义“艺术”被认为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因此我打算从艺术演进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解释这两方面,而不是从艺术概念本身来阐明什么是艺术的问题。
艺术的演进

距今24,000至22,000年的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雕像

公元前大约100年古希腊时期米洛的维纳斯雕像

文艺复兴时期(公元1501-1504年)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

19世纪末罗丹的雕塑:《思想者》
从洪荒远古直到十七世纪,艺术品所表达的主要是艺术家的技艺,因此“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技艺”的同义词,就像“艺术”这个词的本义一样(中文、法文、英文均如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写实主义的出现使得技艺变得更为重要,因为拉斐尔的壁画正是通过透视法将宗教的神圣和世俗的虔诚和谐、平和地表达出来,而米开朗基罗的雕像也正是通过解剖学才表达出人类的健美或力量。对于达芬奇来说,艺术不过是技艺的展现。从十七世纪以后,“美感”开始成为艺术作品的欣赏对象和艺术活动至高无上的追求,而艺术也就更多地与艺术家对美的创造能力相联系。“艺术”从此分化为较高尚的“美术”和较实用的“工艺”,而“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术”的代名词。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推动了个性解放与自由,最终在十九世纪晚期导致了一系列现代艺术运动的出现。到二十世纪,艺术越来越被认为是激发、表现、表达、传递个体或群体“观念”(精神、哲学、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手段,尽管早在古希腊文化中就出现了对人体的崇拜,而在中世纪艺术中圣经是非常重要的题材。虽然在历史上对于到底哪些可以被包括在艺术范围内是有争议的,但大体上公认创造力和技巧性是艺术家所必需的。
从艺术演进的这个非常简要的过程来看,中国赏石显然具备了其中任何一个基本要素:技艺、美感、观念。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赏石是艺术。具体论证如下。
首先,中国古代赏石从拣选、凿取、修治、摆置到配座等都需要一定的技艺,而这种技艺,因为石的情形不同,不能够完全重复地运用而需要相当程度的创造力。文献记载有谓“採集者需择其巧处断取”,“度奇巧取凿”,“相度取材”,“稍有巉巖特势则就加镌砻取巧”,“须籍斧凿修治磨砻以全其美”。这种技艺需要培养和训练,因此欧阳修称“不经老匠先指決,有手谁敢施镌鑱”,而且需要达到较高的水准,才能“雕鑱刻画出智力,欲与造化追相倾。”即使像摆置这样比较简单的问题,同样需要丰厚的经验和熟练的技巧,宋徽宗《祥龙石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祥龙石图》为宋徽宗“凭彩笔亲模写”,因此应该真实地记录了“祥龙石”的形象。从弹窝、孔洞、峰峦的方向看,“祥龙石”实际上是平卧横峰,但通过以底为背的竖立方式,艮岳中的“祥龙石”便呈现为立龙的形象。这显然为欣赏“祥龙石”提供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角度,是一次绝妙的艺术创作。

宋徽宗《祥龙石图》

其次,中国赏石不仅具有独特的美感,而且到宋代已经发展出一套美学理论。宋代的赏石美学建立在石的本体上,注重石本身所具有的形式美:形状的嵌空多姿、表面的纹理纵横、质地的坚润细腻、颜色的丰富多彩。作为宋代著名的赏石家,米芾基於赏石的“形状”和“表面”特征提出了“相石四法”作为赏石审美标准:“瘦、秀、皱、透”(研究者对此有颇多争议)。后人李渔解释称:“言山石之美者,俱在透、漏、瘦三字。此通於彼,彼通於此,若有道路可行,所谓透也;石上有眼,四面玲珑,所谓漏也;壁立当空,孤峙无倚,所谓瘦也。”现存江南三大名峰中,苏州的“瑞云峰”为“透”的典型,上海的“玉玲珑”为“漏”的典型,杭州的“绉云峰”为“瘦”和“邹”的典型,它们就是这种赏石美学理论的体现。

苏州“瑞云峰”

上海“玉玲珑”

杭州“绉云峰”
最后,中国赏石在不同时代凝聚了不同的观念。唐宋时代,受老庄哲学和道禅思想的影响,文人雅士如梁漱溟所说,“爱好自然而亲近自然”,“善於融合於自然之中”,追求清净恬淡、高雅闲逸、自然澹泊、超尘脱俗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而赏石体现的“山岳情结”就是这种情趣的凝结,所谓“高人好自然,移得它山碧”。在唐宋文人的赏石活动中,欣赏者怀有山岳情结,赏石遂采取“山”的形态,以此隐喻、暗示、象征高山大岳,所谓“本向他山求得石,却於石上看他山”。赏石凝重的山岳气势和深邃的天然野趣,激发了赏石者不尽的想象,“名山何必去,此地有群峰”,“从此频吟绕,归山意亦休”。在这样一种“赏石—赏山—游山”的情结传递过程中将赏石者带入一个全新的意境,仿佛置身其中;而赏石者便陶醉於这意境中“意味”的领悟、感受和欣赏。这何尝不是一种高尚的“审美快愉”呢!唐代白居易《太湖石记》故云:“三山五岳,百洞千壑,罗缕蔟缩,尽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为公适意之用也”。
法律的解释
如果上述艺术的演进对我们稍嫌遥远,现实中法律的案例也许能直接地帮助我们判定什么是艺术。1892年,在美利坚合众国对Perry一案中,被告进口了描绘《圣经》题材的彩色玻璃窗,海关按“彩绘玻璃窗”征收45%的关税,而被告坚持认为应该按“油画或水彩画”缴纳15%的关税。最高法院最后以彩色玻璃窗具有较高的实用性、较低的观赏性为由驳回了被告的诉求。在这一案例中,“观赏性”构成艺术品的基本标准,“观赏性”与“实用性”构成负关联的关系,即“观赏性”越强,“实用性”越低,“观赏性”越低,“实用性”越强,因此“实用性”构成非艺术品的标准。
这个标准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发生了变化。1916年,在美利坚合众国对Olivotti一案中,被告进口了模仿古希腊艺术的大理石瓮,海关按“大理石产品”征收45%的关税,而被告坚持认为应该按“雕塑”缴纳15%的关税。海关法院最后审理认为:“美”本身不足以界定一件作品是不是雕塑:雕塑属于模仿包括人体在内的自然物的艺术,它通过雕刻表现了自然物的“真实比例”。在海关法院看来,“真实性”构成艺术品的基本标准,雕塑如果“真实模仿、表现自然”,便是艺术,而这件大理石瓮显然没有艺术地表现人体的“真实比例”。

《空间里的鸟》
然而,法律对于艺术的界定很快就遭到了方兴未艾的现代主义艺术的挑战。1926年,在Brancusi对美利坚合众国一案中,《空间里的鸟》的买家对海关按“金属制品”而不是“艺术品”征收40%的关税提起上诉。该作品的艺术家Constantin Brancusi没有出庭聆讯,而是由其他艺术家、批评家及博物馆馆长代为出庭作证,他们一致认为《空间里的鸟》是一件艺术品。海关方面则参照1916年的案例中确定的艺术必须在“真实比例”上表现自然物的概念,要求辩方证明这件雕塑“模仿了真实的鸟”。海关法院审理后认为:这件作品虽然并非“真地像”一只鸟,但考虑到抽象表现主义在美国艺术领域的现状,况且这是一件“美丽且对称”、“非常悦目”的“原创”作品,因此它应该是一件艺术品。在这个判例中,法庭虽然没有给出“艺术”的新概念,但法庭从“艺术标准”转向“艺术现状”,接受抽象形式的艺术,承认抽象艺术中的“美感”和“观念”,表明法庭对“艺术”开始持有一种开放的态度。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一判例的积极作用,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和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在这个案例第二年后相继开业,从此开启了蓬勃的美国现代和当代艺术。
毋庸赘言,中国赏石同样符合法律上对艺术“美感”与“观念”的界定,因此我有现实的理由认为,赏石是艺术。我相信,如果我们携带赏石进入美国,这些赏石一定是免于关税的,因为它是艺术品!
艺术演进是从专家的角度,而法律案例是从非专家的角度判定何谓艺术。如果赏石从这两个角度都符合艺术的标准,那么我们对于赏石是艺术的结论就应该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就我个人而言,在对艺术的理解上,我属于表达主义者。我认为,一个活动或作品是艺术活动或艺术作品,当且仅当它从视觉(就视觉艺术而言)上提出或回答了这样两个问题:它表达了什么?它如何表达的?赏石的创作者以石为媒介,通过选择、凿取、修治到摆置等一系列技艺,表达出一种自然观和人生观,为欣赏者提供了一种自然的、和谐的美的感受,因此,赏石的创作活动属于艺术活动,其作品也就属于艺术作品。因此,我坚信赏石就是艺术(未完待续)。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丁文父):赏石艺术的审美疲劳:赏石是不是艺术?
本文发布者:玩石迷,获取最新内容,请点此关注《顽石有灵》微信公众号。 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anshime.com/21795.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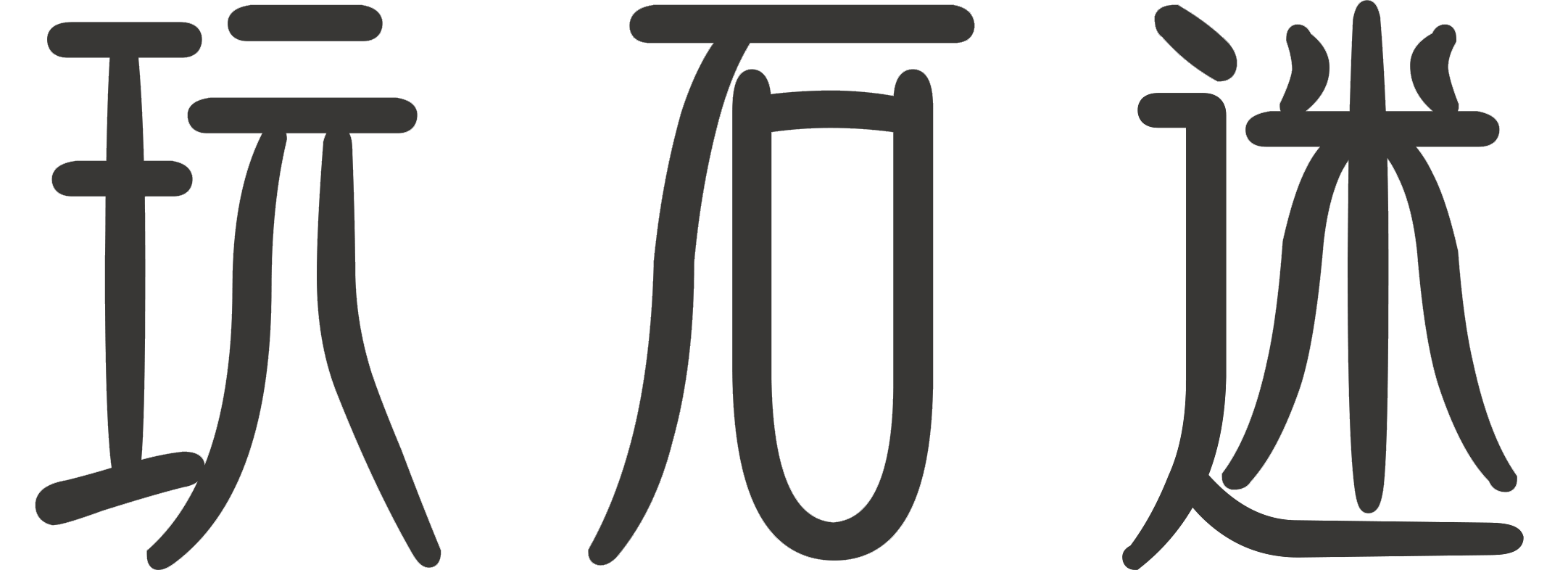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