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晖兄的《明代大理石屏考》(山东画报出版社2018年2月版),在第二章弘治“六 同年图卷”中,注意到故宫博物院所藏明代佚名《五同会图》画中的大理石屏,“庭院石屏后,设一石几,……石桌景深处,先是两函古籍,而衬托书函天青色的,赫然是一具云山纹理的黄花梨框大理石屏!虽只露半幅,但气息高雅,弥漫一卷。”

故宫藏《五同会图》
《五同会图》描绘的是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五位苏州籍高官在京城的雅集活动,包括礼部尚书吴宽、礼部侍郎李杰、南京左副都御史陈璚、吏部侍郎王鏊及太仆寺卿吴洪。所谓“五同”,按照吴宽当年所写的《五同会序》,即“同时也,同乡也,同朝也,而又同志也,同道也,因名之曰五同会,亦曰同会者五人耳”。这五位官至二三品的朝廷重臣,都出自苏州府,吴宽、陈璚为长洲人,李杰为常熟人,王鏊为吴县人,吴洪为吴江人。

故宫藏《五同会图》局部
不过,不知道蒋晖兄有意还是无意没有提及到,《五同会图》中吴宽、李杰坐着的罗汉床,其三围所镶嵌的隐约山水图纹,应该也是大理石。当然,可能因为未见原作,图片像素又不够大,所以不敢轻易判断。

故宫藏《五同会图》石几上有大理石屏
有意思的是,据记载,《五同会图》当时共绘制了五幅,分藏于五位参与雅集的画中主人公。除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件之外,据报道上海博物馆也有一件,惜未见公开发表和展览。

国家博物馆“妙合神形”特展内景

观众在国博参观“妙合神形”特展
前不久看到报道,北京国家博物馆举办“妙合神形——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肖像画展”特展,其中也有一件明代无款《五同会图卷》。此次赴京应邀参加保利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吴彬《十面灵璧图卷》特展学术研讨会”,抽暇参观了国博的特展,得以近距离细观这幅人物画精品。

国博藏《五同会图》
这件国博藏品为绢本设色(40.2X191.5cm),构图与故宫博物院、上博所藏的大同小异,但设色与景物稍有不同,应该也是五幅中的一幅。画面上的石案上,也有一座半遮半掩的大理石屏,不过,其屏芯白质黑章的山水图纹更加确定。尤其是罗汉床三围所镶嵌的大理石,黑白分明,云山意象非常凸显。

国博藏《五同会图》局部

国博藏《五同会图》罗汉床局部

国博藏《五同会图》石几上的陈供
这座明代罗汉床的材质,有点像剔红漆木家具,框架雕刻有如意纹饰,这在当时可能属于宫廷家具制式,品级很高。晚明屠隆在《考槃余事》“榻”中有如此介绍:“有大理石镶者,或花楠者,或退光黑漆,中刻竹,以粉填之,俨如石榻者佳。”可见,明代确实有楠木或者漆木镶嵌大理石榻(罗汉床)者。
在大约万历年间所作的无款《上元灯彩图》(台湾私人藏)中,金陵元宵集市地摊上也有大理石镶嵌的罗汉床。另外,记录嘉靖四十三年抄没明朝大贪官严嵩家财的《天水冰山录》清单中,计有雕嵌大理石床八张。
当时“五同”聚会最多的地点是在崇文街的吴宽、王鏊两府。从这幅画的人物布局来看,三人站立,两人端坐,其中坐于最右侧(东首)的礼部尚书吴宽应该就是主人公了。所以,这座镶嵌云山图纹大理石的罗汉床应该属于吴宽家中的。吴宽是明成化八年(1472年)状元,也是明朝苏州所出的第二位状元,曾侍奉孝宗读书。他诗文书法兼擅,又富藏书,是当时词臣中声望最高的一位,《五同会图》成画时年69岁,第二年七月便卒于任上,明孝宗追赠其太子太保,谥号“文定”。这幅画卷所描绘的,应该也是吴宽参与的“五同会”之最后一次。

明代吴宽书法取法东坡,这是行书《灯下观白氏集简济之君谦二友》
《五同会图》的人物布陈乃至周遭环境,与明代正统年间宫廷画家谢环《杏园雅集图》的图式十分相像,包括石案上的文玩陈列也是大同小异,尤其是谢环《杏园雅集图》(大都会本),在石桌上描摹一方带有山水图纹的大理石砚屏。此外,《杏园雅集图》(镇江本)中也有罗汉床的描绘,其三围镶嵌的隐约为山水图纹,是否就是大理石不敢确认。

明代谢环《杏园雅集图》(镇江本)有罗汉床描绘
杏园雅集发生于明代正统二年(1437年),五同会则是发生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两者都发生在京城,相隔有六十多年,可见,当时大理石制屏(砚屏或座屏)确实已经在士大夫圈中流行了。
国博所藏的这幅明代无款《五同会图》,卷首前面裱边外有画中五人的简历介绍,末尾注解:“按匏庵(吴宽号匏庵)先生卒于宏治十七年甲子七月,年七十,距此图作序仅一年耳。……”虽然没有署名,但应该是清代乾隆及以后藏家的书款,因为弘治年号被写作宏治,绝不是通用或是通假,而是为了避讳清高宗之名弘暦。
又如,明代神宗年号萬暦,后世也有被写作萬歴者,其实暦与歴两者(简写皆为历)也不能混用,也是为了避讳清高宗弘暦。所以,凡是写作萬歴者,应该也是乾隆及以后的写法。这也是鉴定有关古籍版本和书法(刻款)年代的重要依据。

明代吴彬《十面灵璧图》上海预展现场
如此次保利十五周年推出的重磅古代画作,明代吴彬和米万钟书画合璧《十面灵璧图》(又称《岩壑奇姿》)长卷,其中有两处万历年号落款,万历写法并不一致,却反而证明其无懈可击。一处是“十面灵璧”主人书画家米万钟在画后题跋落款中提到:“时萬暦庚戊(1610年)中秋,书于湛园之石丈斋。”这里萬暦的暦字是正解。另一处是清代咸丰二年重臣耆英在画后的题跋,其中写到:“壬子(1852年)冬偕湘翁在静轩斋中小酌,出示明萬歴吴文仲氏为米隐庵氏所绘石图。”此处萬歴的歴字写法,显然是为了避讳清高宗弘暦。

明代吴彬《十面灵璧图》清代耆英画后题跋(局部)

明代吴彬《十面灵璧图》米万钟画后题跋(局部)
有意思的是,吴彬另有一幅画给米万钟的《山阴道上图》长卷(上海博物馆藏),曾经清宫旧藏,卷首有乾隆御题诗,画后有乾隆、嘉庆的收藏印。吴彬在画卷末的山石上,有一篇题跋,叙述了他与米万钟之间的友情,十分难得,最后落款处为“时萬暦戊申(1608)岁冬日,枝隐生吴彬识。”其中的暦字,下部的“日”被白粉涂抹不见了,明显是清宫词臣为了避讳弘暦而为。这也是一种“文字狱”。

明代吴彬《山阴道上图》落款处
大理石屏,在明代上流社会无疑已经作为财富(奢侈品)的象征。在明代绘画中频频出现的大理石屏及家具镶嵌制品,无疑反映了这种倾向。明末文人鉴赏家文震亨曾经指出:“屏风之制最古,以大理石镶,下座精细者为贵。”(《长物志》卷六)也就是认为,大理石镶嵌屏风(砚屏或是座屏)最好,这应该也是大理石镶嵌家具制品的最早形式。至于大理石镶嵌桌榻,时间上应该还要晚一些。有意思的是,文震亨对于桌榻家具镶嵌大理石的做法,表示出了不屑:“古人以相(通镶)屏风,近始作几榻,终为非古。”(《长物志》卷三)
案《长物志》成书于崇祯七年(1621年),距离《五同会图》隔了两个甲子,文震亨还特别强调了大理石“近始作几榻”。文震亨的言外之意可能是,屏风类属于清赏品,几榻类属于实用物,两者自然就有高下之别,将天然石画镶嵌物的清赏、实用功能不加区别,显然不合规制。由此来看,明弘治年间《五同会图》描绘的床榻镶嵌大理石的做法,应该在当时还比较罕见。

明代《五同会图》展览现场
本文发布者:玩石迷,获取最新内容,请点此关注《顽石有灵》微信公众号。 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anshime.com/45797.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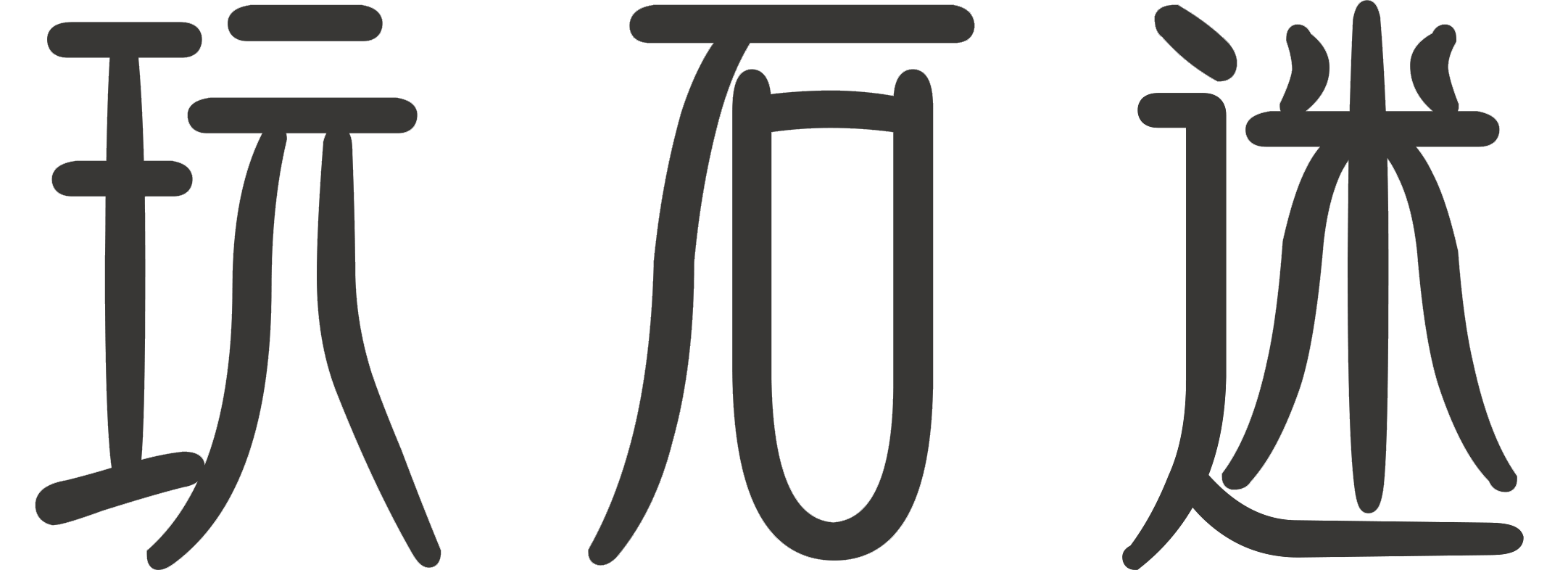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