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比较一般的意义上(内涵)回答了“赏石是不是艺术”的问题,现在我们比较具体地回答第二个问题:赏石是什么样的艺术?这也是有关赏石在艺术中的归类问题(外延)。通过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对于“赏石是艺术”这一问题可以有更丰富的认识。
狭义的艺术通常划分为“雕塑”与“绘画”艺术(建筑现在已经从艺术中独立出来)。作为一个艺术门类,赏石既是立体造型的,因此属于雕塑艺术,例如太湖石或灵璧石等,又是具有“画面”的,可以像绘画作品那样欣赏,例如大理石和雨花石等。由此可见,中国赏石既是雕塑的也是绘画的艺术。
赏石的雕塑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它的绘画性通常体现在一些特殊的画面石种上,并且需要具有对绘画的理解力才能欣赏。宋代就已经发现有一类赏石,其平面纹理变化有若自然山水,极富画意,多用作石屏,所谓“石文可以屏”。宋代诗词中对这种石屏多有记载。苏舜钦《永叔月石砚屏歌》:“桂树散疏阴,有若图画成。”苏轼《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何人遗公石屏风,上有水墨希微踪。”苏辙《欧阳公所蓄石屏》:“石中枯木双扶疏,粲然脉理通肌肤。剖开左右两相属,细看不见毫髮殊。”曾丰《余蓄石屏风》:“巨灵神手造江山,潜写为图置石间。岁久石为图所变,一重峦下一重湾。”舒岳祥《潘少白前岁惠予零陵石一片》题云:零陵石一片,方不及尺,而文理巧秀,有山水烟云之状,予以作砚屏。诗云:“白云际天隅,峰峰争秀出。浩浩水石滩,归鸟时灭没。我欲茅三间,巢此重叠峰。我欲舟一叶,钓此苍茫中。君从何处得此石,千岩万壑在方尺。李成范宽格深秀,关仝荆浩骨峭特。殆非一人之所能,欲穷其源不可得。君言此物出零陵,远近来去皆天成。”
广义的艺术通常划分为“视觉”与“听觉”艺术。赏石不仅属于视觉艺术(即上述雕塑与绘画),而且可以从听觉上欣赏。“音”是赏石不可或缺的欣赏要素,唐宋文献中对此有不少记载可证。
《太湖石志》等所记太湖石“扣之铿然,声如磬”,“叩之五声八音足,疑有僊风摇珮環”。牛僧孺、白居易、刘禹锡三人共咏的太湖石“清越扣琼瑰”、“铿锵玉韵聆”。《老学庵笔记》等记英石“扣之声如金玉”。曾丰《乙巳正月过英州买得石山》写得更为生动:“吾之好石如好声,要须节奏婉且清,真成入耳轻连城”,“英石不与他石同”,“其色灿烂声玲珑”。《云林石谱》等所记灵璧石“清润,扣之铿然有声”,“扣之声清越如金玉”。
据Hugh T. Scogin, Jr.考证,灵璧石与《尚书》所记“泗滨浮磬”有密切关系。灵璧石自宋代以来被认为是古代先民制作乐器“磬”的原料,所谓“安知可备宫架悬,乐府待之八音足”,而灵璧石的产地很早就称为“磬石山”。灵璧石因其声音清越并与古磬有着密切关系,使得它具备了道德和精神上的正统性,从而在各种赏石中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泗滨之韵,所以为佳”。灵璧石也因此成为文人获得精神愉悦,“聊代洗耳”的“泗滨友”。
现代艺术史通常将艺术划分为“具象”与“抽象”艺术。“石”在早期肯定是作为“山”的形象成为欣赏对象的,但赏石本身的形、表、质、色或线条(轮廓)、空间(孔洞)、表面(褶皱)等造型要素也会被抽象出来,成为纯然形式上的独立欣赏对象。这就使得赏石不仅具有具象性,同时也会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成为具象与抽象兼具的艺术。
宋代艮岳“石皆激怒觝触,若踶若齧,牙角口鼻,首尾爪距,千态万状,殚奇尽怪”,“其余石,若群臣入侍,幃幄正容,凛然不可犯,或战栗如敬天威,或奋然而起又若摟取,其怪状余态娱人者多矣”。宋徽宗《祥龙石图》所绘“祥龙石”,腾涌若虬龙之势,挺然为瑞应之状。这些都是赏石作为具象艺术的实例。相形之下,蔡肇《仁寿图》,佚名《折槛图》,赵碞《八达春游图》所绘赏石则表现出极度变异的形象。与此同时,苏轼《古木怪石图》脱离拟山摹物,开写意之先,向丑、怪、奇等比较抽象的方向发展。在宋代,底座和底盘(盆)已经用於赏石的展示,表明赏石已经完全变成独立的艺术欣赏对象。宋人也逐渐地脱离唐人的山岳情结,抛弃对山、石真实性联系的精神上的追求,这就使得赏石的形象越来越突出形式要素,也越来越向形式化和抽象化的方向演进,成为独立的抽象艺术。

蔡肇《仁寿图》

佚名《折槛图》

赵碞《八达春游图》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丁文父):赏石艺术的审美疲劳:赏石是什么样的艺术?
本文发布者:玩石迷,获取最新内容,请点此关注《顽石有灵》微信公众号。 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anshime.com/23304.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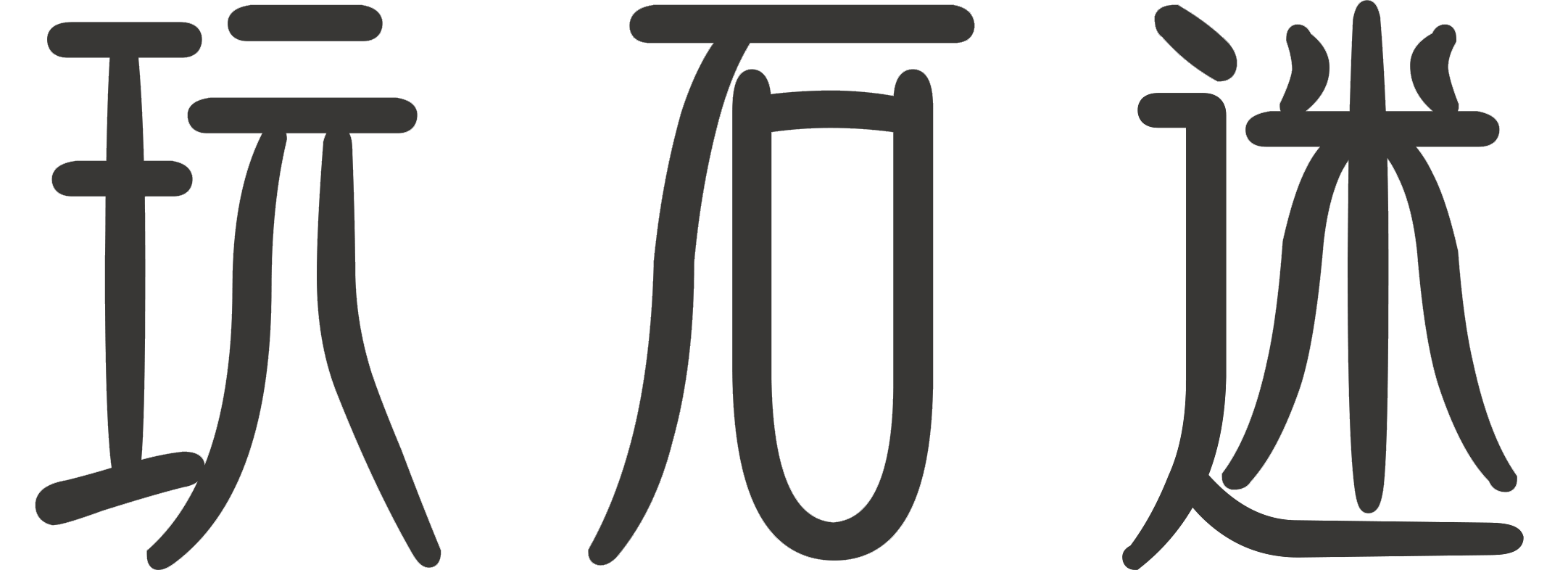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